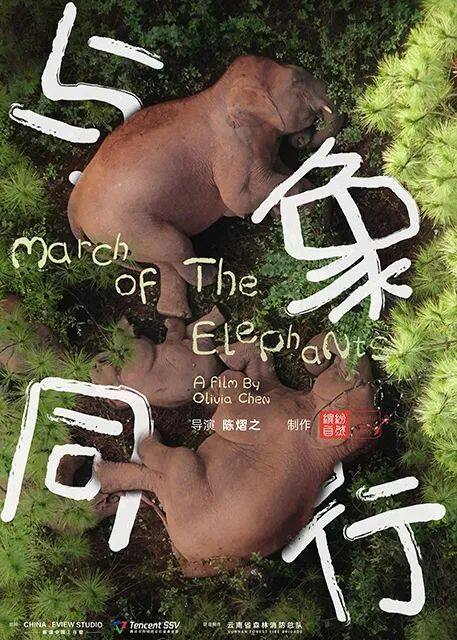- 凤凰十二时辰|一叶单丛茶的时光诗篇
- 让“舌尖上的产业”更有“滋味”!潮安区以科技创新赋能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
- 带上小伙伴来运动!潮安这个“空中运动场”风景独好!
- 累计服务长者约4.68万人次!潮安区打造12个“长者食堂”
- 技术改造助推产业“换道超车”!潮安区积极探索陶瓷产业高质量发展特色路径
- 潮安回应女婴事件:尚未发现虐待,父母抚养意愿强烈
- 聚焦特色产业 打造发展平台 ——探寻潮安不锈钢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进阶之路
- 聚焦“百千万工程” | 潮安区凤凰镇棋盘村持续推进风貌提升工程 打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和美乡村
- 鸭背枇杷惹人爱
- “潮”向未来·高质量发展看潮州 | 潮安区彩塘镇:奋楫“百千万工程” 工业强镇蝶变升级
- 培养环保“小先锋”!湘桥区开展垃圾分类移动科普馆进校园活动
- 电网蝶变!湘桥区磷溪镇埔涵村:“整线成片”大提升 乡村焕新颜
- 筑牢安全防线 共育家国情怀!湘桥区多部门联合开展国家安全教育进校园活动
- 强工业、兴农业、美环境!湘桥区官塘镇多措并举绘就乡村“镇”兴新画卷
- 抢农时 闹春耕 2025年湘桥区春播粮食作物面积预计近2.5万亩
- 湘桥区凤新街道大新乡村:深入推进移风易俗 文明祭扫蔚然成风
- 湘桥区纪委监委:深耕监督“责任田” 护航春耕不误时
- 逐梦“绿美富” 记者乡村行 | 盘活闲置地 “寸土”生“寸金” 湘桥区铁铺镇石板村做活“土地文章”探索富民新路径
- 聚焦“百千万工程” | 湘桥区城西街道仙洲岛:清拆违规建筑 增添乡村新景
- 湘桥区开展学雷锋全民志愿服务专场活动 党建引领“专业社工+志愿服务”
-
 221家潮企亮相第137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,携创新产品展现潮州“智”造的独特魅力。
221家潮企亮相第137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,携创新产品展现潮州“智”造的独特魅力。
 2025年一季度潮州市地区生产总值为313.74亿元,按不变价计算,同比增长5.1%。其中,第一产业增加值为29.93亿元,增长7.1%;第二产业增加值为134.71亿元,增长4.6%;第三产业增加值为149.09亿元,增长5.1%。
2025年一季度潮州市地区生产总值为313.74亿元,按不变价计算,同比增长5.1%。其中,第一产业增加值为29.93亿元,增长7.1%;第二产业增加值为134.71亿元,增长4.6%;第三产业增加值为149.09亿元,增长5.1%。
 在第25个世界知识产权日到来之际,4月25日,由潮州市知识产权局主办的2025年“知识产权宣传周”宣传活动在市图书馆举行。
在第25个世界知识产权日到来之际,4月25日,由潮州市知识产权局主办的2025年“知识产权宣传周”宣传活动在市图书馆举行。
 【千年文脉 烟火潮州】故事里的潮州⑪这条小巷不仅名字好听,甚至还隐藏着最古老的“防盗门”;千百年来,“兴旺安宁”的小巷里承载着一代代潮州人的智慧和希望。本期《故事里的潮州》,一起走进南门十大名巷——兴宁巷。#潮州#兴宁巷#故事里的潮州
【千年文脉 烟火潮州】故事里的潮州⑪这条小巷不仅名字好听,甚至还隐藏着最古老的“防盗门”;千百年来,“兴旺安宁”的小巷里承载着一代代潮州人的智慧和希望。本期《故事里的潮州》,一起走进南门十大名巷——兴宁巷。#潮州#兴宁巷#故事里的潮州
更多美食之城
- 潮州政风行风热线 | 海上养殖需要注意哪些问题?潮州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倾听群众呼声解答热点问题
- 潮州政风行风热线 | 辅助生殖治疗报销如何申请?潮州市医疗保障局为群众解答医保相关问题
- 潮州政风行风热线 丨外来人员如何申请居住证?潮州市公安局为群众解答户政相关问题
- 保障金融权益 助力美好生活 中国人寿潮州分公司联合驻文祠镇帮扶工作队开展“3·15”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进农村宣传活动
- 潮州政风行风热线 丨 5G基站辐射对人体健康有害吗? 潮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为群众解答工业相关问题
- 潮州政风行风热线 | 老年人公交卡该如何办理? 市粤运公司为群众解答公交服务相关问题
- 潮州政风行风热线 丨 老旧小区如何申请加装管道气?潮州深能燃气有限公司为群众解答用气安全及服务等相关问题
- 潮州政风行风热线 丨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如何申请补贴?潮州市商务局为群众解答有关热点问题
- 潮州政风行风热线 丨什么是3C产品及3C认证?潮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为群众解答市场监管相关问题
- 潮州政风行风热线 丨“交管12123”APP可处理异地交通违法吗?潮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为群众解答车辆及交通相关问题












 日报APP
日报APP 日报微信
日报微信